在诺奖作家蒲宁的回忆录里,文豪们如此爱斗嘴斗歌
蒲宁回忆录
1933年诺贝尔文学奖、俄罗斯作家蒲宁曾与托尔斯泰共同探讨生活和写作,与契诃夫保持着亲密的友谊,三度获得俄罗斯文学最高奖项普希金奖,与艺术界众多风云人物往来密切。
在离开俄罗斯之前,蒲宁已然取得了极高的文学成就。1920年初,蒲宁离开俄罗斯侨居巴尔干,后迁至巴黎,此生再未重返俄罗斯。近日由理想国·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蒲宁回忆录》记录了他在俄罗斯“最后的日子”。
这部自传性质的回忆录包括三个部分:1917年—1918年的《蒲宁日记》,讲述了乡村的安宁生活;1918年—1919年的莫斯科—敖德萨日记,书中命名为《该死的日子》,是十月革命后,蒲宁对生活的观察记录;第三部分则是札记与文章的收录,其中不乏对俄罗斯文艺界众多风云人物如列宾、高尔基、叶赛宁、夏里亚宾等的追忆,也有对于人生重大时刻的记录,如参加诺贝尔文学奖颁奖礼的回忆与获奖感言。
在他长达七十年的写作生涯中,这是蒲宁唯一一部放弃古典文学传统,将自己的内心完全表露于外的作品。他在耄耋之年,将暌违多年的音容记忆整理成文,让我们得以窥见当时的俄罗斯文艺巨擘们不为人知的一面,为一个时代写下细密真实的注脚。

《蒲宁回忆录》
[俄] 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蒲宁 / 著
李辉凡 李丝雨 /译
理想国·云南人民出版社 2024年1月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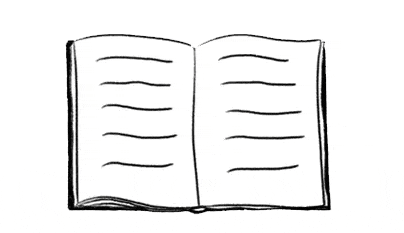
在莫斯科曾经有人说,夏里亚宾同作家们交好,是故意要为难同他争荣誉的索比诺夫。夏里亚宾接近作家们完全不能说明他喜欢文学,只是说明他希望不仅被公认为著名的歌唱家,而且被公认为一个“先进的、有思想的人”。他说过,“但愿狂恋索比诺夫的只是那些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狂恋而且将来也狂恋男高音的听众”。不过,我觉得夏里亚宾接近我们并不都是出于自私的目的。比方,我记得,他是多么热切地想认识契诃夫!关于这一点他对我说过多少次了。我终于问他 :“为什么要见他呢?”
“因为,”他回答说,“契诃夫什么地方都不露面,老是没有机会和他认识。”
“得了吧!这需要什么机会呢?叫一辆车,你就去吧。”
“我可不愿意像一个无耻之徒那样去与他见面!除此之外,我知道,我在他面前是如此畏缩,会显得十足像个傻瓜。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无论如何请你送我去见他……”
我毫不拖延地办成了此事,并确信,他说的都是实话。到了契诃夫家里,他的脸红到了耳朵根,说了几句话,声音又低又不清楚……而当他离开契诃夫家走出来时,却充满狂喜地说 :“你不会相信,我是多么幸福 ;我终于认识了他,他是多么迷人啊!这就是一个人!这就是一个作家!如今我看所有其他的人都会像看骆驼那样了。”
“谢谢。”我笑着说。
他哈哈大笑起来,满街都听得见。

莫斯科文学小组部分成员,1902年,上排左起:斯捷潘·斯捷塔莱茨,费奥多尔·夏里亚宾,叶夫根尼·奇里科夫,前排左起:高尔基,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伊万·布宁,尼古拉·特雷索夫。
有一张很出名的照片—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它以明信片的形式在当时销售了几十万张。在这张照片上拍下了安德烈耶夫、高尔基、夏里亚宾、斯基塔列茨、捷列绍夫和我。有一天,我们一起在莫斯科一家德国餐厅“杜鹃花”吃早饭,吃了很长时间,而且很愉快。突然我们决定去照相,就在这时我和斯基塔列茨首先吵了起来。我说 :“又是照相!老是照相!没完没了的狗婚礼。”
斯基塔列茨生气了。
“为什么是婚礼,而且还是狗的婚礼?”他用一种粗暴的伪装的男低音说,“比方我,从来就不认为自己是狗,不知道其他人是否认为自己是狗。”
“不然又称作什么呢?”我说,“我们一个接一个的宴会、节日,用您自己的话说,是‘老百姓饿得浮肿了’,俄罗斯快要灭亡了,国内是‘各种各样的灾难,下面是黑暗的统治,上面是统治的黑暗’。国家的上空‘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地飞翔’,而在莫斯科,在彼得堡呢?日日夜夜是过节,全俄性质的事件一件接着一件 :新的‘知识’文集,汉姆生的剧本,艺术剧院的初次上演,大剧院的首次上演,高等女校学生看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卡恰洛夫时晕了过去,逞勇闯祸的车夫把车开到雅尔,驶进了斯特列里纳……”
事态可能发展为吵架。不过这时响起了大家的笑声,夏里亚宾喊道 :“好,说得对,我们还是走吧,让狗的婚礼流芳百世!我们去照相,真的,常去照,我们死后,应该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点东西,否则不管怎么唱啊唱啊,等他死了,也就完了。”
“对,”高尔基附和着说,“写啊,写啊,然后就死了。”
“ 例如, 我,” 安德烈耶夫黯然地说,“ 我将首先死去……”
他经常这样说。大家暗暗地嘲笑他。但后来的结果却正是这样。
大家都认为夏里亚宾很左,当他唱完《马赛曲》或者《跳蚤》时,往往会由于高兴而狂叫起来,因为在这些歌里被认为有某种对国王的革命的撒旦式的讥讽。
曾经有过一个国王,
跳蚤跟他一起生活……
可是突然发生了什么事呢?撒旦竟在国王面前下跪了—全俄罗斯都散播着一个传闻 :夏里亚宾在沙皇面前下跪!关于此事的传闻,夏里亚宾感到无尽的愤懑和惆怅,后来又为自己的这一罪过洗刷过多少次啊!
“我怎么可能不下跪呢?”他说,“这是一台皇家歌剧合唱团的捧场戏。合唱团决定向皇帝请求增加薪俸,利用沙皇光临演出的机会,在他面前下跪请求。我也是合唱团的一员,我该怎么办呢?我事先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这次下跪:突然,舞台上的整个合唱团像被镰刀刈了一下似的全都跪下了,双手伸向沙皇的包厢!我怎么办呢?一个人像电线杆那样杵在整个合唱团之上?须知,这也是真正丢脸的事!”

《费奥多·夏里亚宾》康斯坦丁·柯罗文/绘,布面油画,1911年
我在俄国最后一次看见他是在1917年的4月初,列宁已经回到彼得堡的那个时候。这段时间我也在彼得堡,并和夏里亚宾一起收到了高尔基的请柬,他邀请我们参加米哈伊洛夫剧院的隆重集会,会上高尔基将发表关于建立其某某“自由科学研究院”的演说。我不明白,也不记得我和夏里亚宾怎么会收到请柬,去参加这个各方面都称得上是荒谬的集会。高尔基的演说时间相当长,辞藻过于华丽。后来他宣布说 :“同志们,夏里亚宾和蒲宁也在我们中间,我提议欢迎他们!”
大厅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跺脚声,招呼我们。我们躲到了后台。忽然有一个人从我们后面跑过来说 :大厅里大家要求夏里亚宾唱歌。如此一来夏里亚宾又一次要“下跪”了。他坚决地对跑过来的人说 :“我不是消防队员,一经召唤就立即爬到房顶上去。您就这样对大厅里的人们说吧。”
跑过来的人不见了。而夏里亚宾摊开双手对我说:“瞧,老兄,这是什么事呀!唱不行,不唱也不行——到时候就会想起你,把你挂在灯笼上,真见鬼。可我还是不打算唱。”
于是便没有唱。在布尔什维克时代,他的胆子已没有那么大了,所以他最终巧妙地从他们那里跑掉了。

1914年列宾为夏里亚宾画肖像
1937年6月我在巴黎最后一次听他唱歌。他开了音乐会,时而独唱,时而与阿索斯合唱团合唱。我想,他当时已经病得很重了,激动得不同寻常。自然,他每次演出后都是很激动的—这是正常的。我看见过,在叶尔莫洛夫剧院门前,全体观众是如何晃动和画十字的 ;我看见过,在后台,他演完了连斯基的角色甚至罗西本人的角色后,走进自己的更衣室时,观众简直都要晕倒了!大概,夏里亚宾在某种程度上也有类似的情况,只是观众以前从没有见过罢了。但是在这最后一次音乐会上他们看见了。夏里亚宾则只是由于他的手势和语调的天赋才得到解脱的。他从后台给我捎来一张字条,要我到他那儿去。我去了。他站着,脸色苍白,冒汗,颤抖的手拿着的烟卷在抖动。他立即问我(当然,他从前不会这样做的):“喂,我唱得怎么样?”
“当然是非常好,”我回答道,并开玩笑地说,“好得我一直在给你伴唱呢,并因此而使听众非常愤懑。”
“谢谢,亲爱的,你就伴唱吧,”他带着不安的微笑回答说,“你知道吗,我身体很不舒服,最近我得到山上去休息,到奥地利去。老兄,首要的事是要到山上去。那么你夏天要到哪儿去呢?”
我再次开玩笑说 :“就是不到山上去。我现在就一直在山上,时而是在蒙马特,时而是在蒙帕纳斯。”
他又微笑了一下,却有点儿没精打采。
他为什么要举办这最后一次音乐会呢?也许是由于他已感觉到自己就要离去了,于是便想同舞台告别一下,而不是为了钱,尽管钱他也是喜欢的。他从来没有因慈善的目的唱歌,他喜欢说 :“只有鸟儿才免费唱歌呢。”

夏里亚宾自制塑像
我最后一次看见夏里亚宾是他逝世前的一个半月——我和玛 · 阿 · 阿尔达诺夫一起去看望了生病的他。他当时已经病得很重了,但还是有力量,在他身上还有许多生命和演员的光华。他坐在饭厅角落的圈椅里,旁边点着一盏带黄色灯罩的油灯。他穿着宽大的黑色绸布的病号服和红色的便鞋,额头上高高地竖起一撮突出的额发,高大而又华美,就像一头老狮子。他身上流的是什么血呢?是像罗蒙诺索夫身上的,瓦斯涅佐夫兄弟身上的俄罗斯北方特有的血吗?青年时期他的外表是极其平民化的,但是年复一年,逐渐地变了。
托尔斯泰第一次听到他唱歌后说 :“不行,他唱的声音太大了。”
直到现在还有许多自作聪明的人真的相信托尔斯泰对艺术一窍不通,因为“他指责了莎士比亚和贝多芬”。对于这些人我们可以放在一边,但到底该如何理解他对夏里亚宾的评语呢?他对夏里亚宾的歌喉、夏里亚宾的才华的全部价值漠不关心吗?当然不可能这样。托尔斯泰只不过是对他那些优点保持沉默罢了,他只说出了他觉得是缺点的意见,指出了夏里亚宾身上的确经常存在的那些缺点,特别是当他在二十五岁左右的时候:他各方面的精力过剩,有些漫无节制,故意引人注意等。在夏里亚宾身上,“勇士的动作”太多了些。这既来自他的天性,也是他在舞台上自己养成的性格,而舞台则从青年时代起就是他的全部生活。这种生活每一分钟都在受到群众不停歇的兴奋的刺激。在任何地方,在全世界,群众只要在什么地方看见他—在歌剧舞台上,在音乐舞台上,在著名的海滨浴场,在价位昂贵的餐厅里,或者在百万富翁的沙龙里——都是这样。享受了荣誉的人要做到克制是很困难的!
“荣誉就像海水——喝得越多便越想喝。”契诃夫曾开玩笑地说过。
夏里亚宾“没完没了地喝这种水,并没完没了地想喝”。他喜欢强调自己的力量、豪勇、自己的俄罗斯天性,而且“从一个卑贱的平民变成一个公爵”——这该如评判呢?有一次他给我看了一张他父亲的照片 :“你看看,我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残酷地鞭笞过我!”
但是,照片上他是一个相当体面的人,五十岁左右,穿着浆硬的衬衣,翻领,系一条黑色领带,穿着貉绒大衣。于是我怀疑起来,他父亲真的鞭笞过他吗?为什么这些被大家称之为“天生有才的人”会在儿童时代不断地被“残酷鞭笞”呢?“高尔基、夏里亚宾是从人民的海洋底下升上来的”……真的是从底层升上来的吗?他的父亲在地方自治参议会效力,穿着貉绒大衣和浆硬的衬衣,天晓得是什么样的底层。我想,夏里亚宾在他的回忆录中对其整个儿童时代和少年时代大体上说得有些夸张,当时他生活中的朋友和同事们说得也有些夸张——例如某某铁匠对他的歌唱所说的某些话就过于华而不实。
“唱吧,费佳,心灵上将会更快乐!歌曲—就像鸟儿,你放了它,它就飞了。”
不过,这个人的命运仍然的确是神话般的—从与铁匠的交情到与大公们和继承王位的亲王们的友好宴会,其距离可是不小哩!他的生活在各个方面都是无限幸福的。上帝真正给了他“尘世范围内的一切尘世的东西”!给了他强大健壮的身体,这个身体只是在全世界漫游了四十年,经过各种各样的尘世诱惑之后才歪斜了。

高尔基与夏里亚宾
有一回我和巴蒂斯蒂尼同住在敖德萨的一个旅馆里,他当时在敖德萨巡回演出。他不仅以自己歌喉的年轻的清新气息,而且以其全部的青春活力使所有的人感到震惊,尽管他已经七十四岁了。这种青春的秘密何在呢?部分原因是他对自己的保护 :每次演出结束之后,他便马上回家,喝热牛奶加碳酸矿泉水并睡觉。而夏里亚宾呢?我认识他许多年了,我和他的大多数见面都是在餐厅里。我们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认识的现在已记不起来了,但是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在大莫斯科旅馆里,在伊维尔小教堂对面的一栋大房子里,他把对我的称呼改成了“你”。在这栋房子里,除了旅馆还有一家小饭店,我来莫斯科就住这家饭店,常常住很长时间。小饭店这个词早已不适用于这个价钱昂贵的宽敞的餐厅了。小饭店年复一年地逐渐变成了现在的餐厅,尤其是我住在它上面的旅馆里的那个时期 :当时它就扩大了,里面开辟了一些新的大厅,布置得很阔气,并指定专门供特别高贵的宴会使用,供最著名的莫斯科商人(他们中最欧化的人)夜间狂欢使用。我记得,在那些夜间狂欢的人当中,主角是莫斯科的法国人苏及其太太和他的熟人们。我也坐在他们中间。苏在宴会上,正如常言所说,香槟酒流成了河 ;他时常拿一百卢布的钞票作为茶钱,赏给那不勒斯的乐队,穿着红色短上衣的乐队在枝形吊灯的灯光下一边演奏,一边痛饮。瞧,大厅门口突然出现了黄头发的夏里亚宾的高大身影。他,正所谓用“鹰的”目光,扫了一眼乐队—突然手一挥,就和着乐队的演奏唱了起来。还用说吗,那不勒斯人和所有正在大吃大喝的人在“歌王”这种出乎意料的恩赐下,充满了何等的狂喜啊!那个夜晚,我们几乎一直喝到第二天早晨,后来我们走出餐厅,停在旅馆的楼梯上告别,他突然用那种伏尔加河的男高音对我说 :“我想,万纽沙,你喝得太多了,因此我决定用我的双肩把你背到你的房间里去,因为电梯已经不开了。”
“你别忘了,”我说,“我住在五楼,而且我的个头也不小。”
“不要紧,亲爱的,”他回答说,“无论如何我都要把你背上去。要扮演‘勇士’的角色就要扮演到底—只是求你到了房间之后给我一瓶‘百年的’一百卢布的勃艮第红酒,我发现它很像马林果酒。”
毫不偏颇地说,他花的力气还是相当大的。他不停地说话,不让自己的交谈者开口,不断地说东道西,一切都表现在脸上,随时蹦出几句俏皮话,几个词—多半是最强烈的词,并一支接一支地抽烟,老是摆出“古代勇士的派头”(这是他真正的激情)。有一次我和他坐一辆漂亮马车在冬天夜晚的莫斯科从布拉格饭店奔驰到斯特列里纳饭馆,天气严寒,马车飞速前进,而他却挺直身子坐着,敞开皮袄,大声说话,哈哈大笑,烟卷的火星随风四散。我忍不住大喊一声 :“你干吗要糟蹋自己!住嘴,掩上棉袄,把烟扔掉!”
“你是聪明人,万尼亚,”他用一种甜腻腻的腔调回答我,“你的担心干脆是多余的。老兄,我的血是特殊的,俄罗斯的,什么都经受得住。”
“我讨厌你那俄罗斯的!”我说。
“瞧,又责骂我了。我可害怕责骂 :责骂人,可以把人赶进棺材里去。你动不动就对我说 :‘哎哟,你,善哉,好汉。’为什么呢,万尼亚?”
“为了让你别去穿腰部带褶的男式上衣、上了漆的皮靴和丝织的又高又直的带紫色衬圈的斜领衬衣,别同高尔基、安德烈耶夫、斯基塔列茨一起打扮得像民粹派一样,别和他们一起装出很勇敢的若有所思的姿势去照相—要记住,你是什么人,他们又是什么人。”
“我跟他们有何不同呢?”
“不同在于,例如高尔基和安德烈耶夫都是很有能耐的人,他们写的所有东西往往哪怕甚至是浅陋的,那也是‘文学’,而你的歌喉,无论如何也不是‘文学’。”
“酒鬼也喜欢奉承,万尼亚。”
“这不错,”我笑着说,“你还是住嘴,把皮袄掩上吧!”
“好吧,就听你的……”
于是他掩上了皮袄。突然,他大声地说一句 :“查理有仇敌!”吓得马猛然向前一冲,更厉害地狂奔起来。
当时莫斯科存在过一个文学小组“星期三”。小组每个礼拜都聚集在乐天而富有的作家捷列绍夫家里。在那里我们相互朗读自己的作品,评论它们,一起吃晚餐。夏里亚宾是我们的常客,他听大家朗读作品(尽管并不总能耐着性子),时而弹钢琴,并且自弹自唱,有时唱俄罗斯民歌,有时唱法兰西小调,时而是《跳蚤》,时而是《马赛曲》,时而又是《伏尔加船夫》,使有的人激动得“喘不过气来”。
有一次他来到“星期三”,立即就说 :“兄弟们,我很想唱!”
他打电话给拉赫马尼诺夫,也同样对他说 :“我想唱得要死!赶最漂亮的马车过来,马上来,我将唱整整一夜。”
所有这一切当然有些做作。毕竟也不难想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晚会—夏里亚宾与拉赫马尼诺夫联袂演出。在这个晚会上夏里亚宾相当公正地说 :“对你们来说,这不是大剧院,大剧院也不要听我唱,可是你瞧,在这样的晚会上,我却与谢廖扎在一起。”
有一回他在卡普里岛,在我落脚的克维西桑旅馆做客,也这样唱了歌。我和我的妻子在这个旅馆里一连住了三个冬天。为了给他洗尘,我们设了午宴,请了高尔基和卡普里岛俄国侨民中的一些人。午宴后夏里亚宾应邀唱歌,于是又成了一次十分令人惊讶的晚会。在饭厅里,在旅馆所有华美的客厅里,旅馆里的客人们和许多卡普里岛的人聚集在那里,他们带着狂热的目光,屏着呼吸听着……有一次在巴黎,我在他那里吃了早饭后,他自己还提起了这次晚会 :“记得吗,我在卡普里岛你的家里是怎么唱歌的?”
然后他打开留声机,放自己过去的唱片,热泪盈眶地听着,小声说道 :“唱得不错!但愿一切如此!”
新媒体编辑:傅小平
配图:历史资料

原标题:《在诺奖作家蒲宁的回忆录里,文豪们如此爱斗嘴斗歌|夜读·倾听》

